(營口之窗“營口故事”)菊 花 憶
張冰
北方的鄉村一進初冬就沒有什么景色了,每下一場小雪兒天氣就涼了幾分;田野里灰蒙蒙的,樹枝上沾著的幾片黃葉,戀戀不舍地落下了;侯鳥們急忙地遷移到南方去了,剩下幾只麻雀在房前屋后呻吟著:“什么時候才能熬過這鬼天氣呢?”
但在我家院子的那兩盆秋菊好像沒有什么感覺似的,開得更加旺盛了。黃色的花朵沾上潔白的雪兒,顯得格外鮮艷了。
從我記事那天起,母親就愛擺弄一些花兒。她把家里閑置的一些壇壇罐罐盛滿了土,栽上一些花草讓我們欣賞著。其實沒有什么特別出名的花兒,那兩盆秋菊還算不錯的。每年一開春母親就忙碌著,好像是一種寄托似的。
我讀中學的時候,家里的生活比較拮據,經常靠表舅和二姨家接濟。父親有時心情不好,時常把花盆砸碎了,花兒揚得滿院子都是。好在都是些草本花兒,生命力還是很頑強的。父親過幾天消氣了,母親又種了一茬,盡管稍晚了一些,秋末冬初也能聞到花兒的芳香。
在眾多詠菊的詩詞中,母親最喜歡明代詩人于謙的那首《過菊江亭》的詩:“杖履逍遙五柳旁,一辭獨擅晉文章。黃花本是無情物,也共先生晚節香。”
母親喜歡菊花是為了調解心境的。她6歲的時候,我外婆就去世了,她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太姥姥家渡過的。舅姥爺(母親的舅舅)待我母親像親女兒一樣,她與我二表姨一起進了私塾讀書習文,母親的學業很出色,她能背誦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家詩》、《三字經》,還能通讀《紅樓夢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游記》、《三國演義》等名家名著。在那個年代,母親純粹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化人,也是遠近聞名的“小才女”。
母親對我說,從周朝至春秋戰國的《詩經》和屈原的《離騷》都有菊花的記載。有詩云:“朝飲木蘭之墮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菊花與中華民族的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我家原是一個大家族,曾祖父帶領祖父及父輩們艱苦創業,除了耕作農田外,還開墾了百畝鹽田,創建了“遼東灣鹽業商行”,白花花的食鹽銷往全國,包括延安等革命根據地,也通過海上銷往東南亞及歐洲一些國家和地區。“張氏家族”在本地區赫赫有名,也謂遠近聞名的“資本家”。
一九三四年父親與母親結婚,那時的家業正是旺盛時期。父親號稱是張氏家族的“三少爺”,在外人眼里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。
日本占領東北后,家族的鹽業被日本人霸占了,美其名曰叫作“合作經營”,其實都是日本人說了算。小鬼子投降后,國民黨政府以“通共”的罪名將我家的鹽田沒收了,從此張氏家族徹底破產了。
一九四六年初,以我父親為首的叔侄六人一起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,決心不推翻國民黨政府不回家。
菊花屬于草本植物,她分地上莖和地下莖兩部分。花期過后,地上莖大多都枯死了,次年春季由地下莖發生孽芽。母親每年開春就忙活給盆里的發芽根澆水施肥,期盼立秋時節能聞到菊花的清香。
父親參軍后,母親帶著四個孩子在家度日,那時,大哥張耀千10歲、二哥張耀田8歲、姐姐張素仙5歲、三哥張耀文2歲,還有母親懷里懷著的四哥沒有出生。
那個年頭,可謂山河破碎,風雨飄搖,民不聊生。一九四七年的冬天,未滿6歲的姐姐就餓死了。聽母親講,那一天格外寒冷,外面飄著雪花,家里一粒糧食都沒有。姐姐瘦得只剩一層皮包著骨頭了。她說了一聲:“媽媽我餓”,母親喂了一口水她就咽氣了。那年大哥才11歲,骨瘦如柴,沒有力氣抱著姐姐,埋她的時候,哥哥只好拽著姐姐的兩條腿在雪地上拖著,葬在房后的壕子里了。據哥哥講,當時把姐姐后腦的頭發都拖掉了。
每每想起母親講述這段悲慘遭遇,我不由得仰天長嘆,肝膽欲碎,淚如泉涌。什么人能承受了這樣凄涼的場面呢?那是我的母親,我那未滿32歲的母親……
一九四八年初,正是國共兩黨“拉鋸”的時候。為了爭奪營口這個戰略要地,兩軍進進出出又出出進進,周邊的老百姓更是民不聊生、苦不堪言。聽母親講,左鄰右舍的幾個村幾乎天天都在死人,餓死的孩子隨處可見。
這一年,我四叔來到我家,跟母親說:“這樣下去,幾個孩子都得餓死,我帶耀田出去要飯吧。”母親沒有答應。后來在四叔的再三勸說下,母親為了二哥活命只能默許了。
二哥那年10歲。臨走之前,母親給他縫改了一件舊衣裳,在胸前做了一個“大兜兜”,告訴二哥:“要到東西就往大兜里裝。”二哥說:“媽媽,我會要好多好多東西的,帶回來給你吃”。
臨走的那天,母親再三囑咐四叔,一定要照顧好孩子,四叔也表態:“寧可我受苦,也不讓孩子受委屈。”母親含著淚水,送到村口,望著遠去的四叔和二哥的背影,久久不肯離去……
那一年,母親身懷八個月的四哥就要臨產了。大哥跟母親說:“媽媽,咱倆不出去要飯,在家就得餓死。”母親一把抱住哥哥,放聲大哭:“大兒子懂事了。等媽媽生下你小弟弟后,我們娘仨一起走。”
一個月后,四哥降生了。那時家里沒有一點可吃的東西,母親生下四哥的第六天,只好忍著身體的疲憊及疼痛,抱著剛出生的嬰兒、帶著哥哥離開家鄉,蹣跚向北逃生。
聽母親講,當時天氣很冷,產后的血水一直流到腳后跟。那種痛苦是常人無法忍受的。
走了大半天,到了大石橋。當時的大石橋火車站前,來往的人比較多,有做買賣的、有趕集的、有要飯的、有賣孩子的……一片凄涼的景象。
大哥穿著破衣爛衫,餓得躺在馬路牙子上。一位趕大車的中年男子,見到哥哥的樣子,用腳踢了一下哥哥的腦袋說:“這孩子死了吧?”母親說:“沒死,是餓的。”于是,那位好心的男子,從車上的馬槽子里拿出一小塊豆餅送過來,母親把那塊豆餅泡了一些水喂了哥哥,哥哥才緩過來氣。
這時候,我遠房的一位舅舅叫冷守成,他在火車站前拉小活,看到母親悲慘的樣子,便勸母親說:“表妹呀,還是把懷里的孩子送人吧,讓孩子有個活命吧。”
那時候,真是叫天天不應,叫地地不靈呀。母親想:“自己的親骨肉,怎么能送人呢?”。又想“剛生下幾天的嬰兒,沒有奶吃,早晚也得餓死”。在表舅的勸說下,母親只好把懷里抱著的四哥送人了。
四哥被抱走的那一刻,母親抱著大哥放聲大哭,當時圍觀的人無不傷心流淚。
母親說,菊花是花中四君子之一。她最可貴的是不與春蘭爭艷,也不跟夏荷竟輝,更不與牡丹媲美,只是在百花凋謝的時候,解除人們對悲秋的失意感罷了。
離開了大石橋,母親帶著哥哥一直往北走。娘倆兒,破衣爛衫、風餐露宿,走一道、要一道,人間疾苦嘗到了盡頭。
那年深秋,母親帶著哥哥乞討到海城縣境內。一天傍晚哥哥突然發高燒不省人事,母親把他抱到一家門前的大榆樹下,用手扒榆樹皮,一口一口地嚼著喂哥哥。過路的人都搖頭:“這孩子肯定不行了。”母親哭著喊著,沒有一個人應聲的。
就在母親求生無望的時候,村里的一位好心人端來一碗玉米湯糊過來了,對母親說“讓孩子喝了,看能不能救活。”母親趁熱把湯糊喂給哥哥,過了好一會兒,哥哥才慢慢地睜開了眼睛。經過母親六七天的照料,哥哥總算活過來了。
一九六五年春天,哥哥參加全省四級干部農業拉練會,正好來到他討飯時的村莊。他看見那棵大榆樹時放聲大哭。在場的人都莫名其妙,省領導上前問他哭什么,哥哥如實把他當年隨母親討飯時的情景敘述了一遍,在場的人都落淚了。
據母親講,哥哥拉練回來,大病三天三夜,這里面包含著多少童年、少年的心酸與苦辣呀。哥哥的心情是常人無法理解的。
父親參軍后,經歷四次大小戰役,著名是遼沈戰役。在攻打錦州時,父親所在的連隊部署在塔山,負責阻擊南線增援錦州之敵。據父親講,國民黨軍從陸地、海上展開了階梯式的輪番進攻,上有飛機轟炸。戰士們的鮮血染紅了山崗。經過四天四夜激烈戰斗,確保了錦州戰役的勝利。塔山阻擊戰傷亡慘重,我父親所在的團只剩下二十幾人。
全國解放了,父親也復員了,母親領著哥哥回家了。過了不長時間,四叔也回來了,但只是他一個人回來的。我二哥哪去了?母親不停地追問。四叔嘴里總是吐出兩個字“死了”。母親有些不相信,整天以淚洗面。
我四叔是一個老光棍子,一輩子沒娶親,晚年跟村里的一個小寡婦打伙過了幾年。用當時的話講,四叔就是一個游手好閑之人。
過了好多年,老家捎來信兒說四叔病危,母親去看他。那時四叔已經不省人事了,母親又追問他:“老四,你都這樣了,快告訴我耀田真的死了嗎?”四叔慢慢地緩了一口氣,用微弱的、幾乎讓人聽不清的聲音說:“對不起三嫂,耀田讓我賣了,賣了6塊大洋。”母親急切地追問,“賣到哪里了?什么地方?”“賣到西豐縣了。”說完,四叔就咽氣了。
母親回家后,整整病了一個月。每到大年三十晚上,她總是默默地流眼淚,母親失去的太多了。
一進入深秋季節,其它的花兒都凋謝了,唯有那兩盆秋菊在庭院里掩映著。哪怕是花朵開的不那么嬌艷,母親總是耐心地侍候著。一次我隨便摘了一小朵,母親不高興了,便對我說:“天氣這么冷,開一朵花不容易,哪能說摘就摘呢。”我理解母親的心思,從那以后再也不摘花兒了。
我上大學走后,總是惦念著母親和她栽的那兩盆秋菊。一次,我做了一個夢:母親在庭院里侍弄花兒,突然暈倒了不省人事,我被驚醒了,出了滿身冷汗。第二天也沒心思上課了,總想請假回家看看。后經同學解夢說:“做夢都是相反的,老娘保證沒事兒。”我的心兒才慢慢地靜了下來。
放寒假回家,那兩盆秋菊已經凋謝了,但葉片還是綠綠的。母親對我說:“今年的菊花開得又大又鮮艷,還給鄰居移栽幾棵呢。”我怕母親太勞累了,不想讓她再擺弄花了。一次,我到商店里買了幾束塑料菊花插在花盆里,母親只是笑了笑沒有說話。過了幾天塑料花不見了,我仔細找了找,讓母親放到裝糧的庫子里了。母親說:“菊花還是真的好,在寒冬的季節,她蘊藏著春的氣息,又能解除苦悶的心境。”我十分理解母親的心。
我要畢業的那年暑假,幾個同窗好友回鄉后約到蓋州市楊運鄉同學家游玩,也算避暑吧。
楊運鄉位于遼南中部,屬于長白山末脈。那里山清水秀,氣候宜人,可謂避暑的好去處。每到夏季多有學者、騷人到那里休閑渡假或吟詩作賦。
而不料的是,我們一到楊運鄉天氣就變了:天剛剛變黑就下起了小雨,后來變成了中雨、大雨……山洪爆發了、鐵路沖斷了。一時間整個山村被洪水沖刷得干干凈凈,我們拼命逃到山坡上,沒來得及跑出的人大部被洪水沖走了。
楊運發大水的消息迅速傳開,母親知道后,整天以淚洗面。半個月過后,我與另一位同學走出了災區,“平安”地回家了,但母親的右眼永遠地失明了。
兩盆秋菊發芽、開花,開花、落葉,一晃兒幾年過去了。我畢業被分配到當地的一所中學教書,后又調到區里工作。那時工作比較忙,但我每次回家都細心地幫助母親拾掇拾掇那兩盆秋菊。臨走時,母親總是念叨著:“不要辜負國家,要好好工作……”她拄著棍子,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,已經看不見我的影子了,還不肯回去。
有一天,我到鄉下研究廣播電視網絡建設工作,順便回老家看看母親。母親拿著眼鏡對我說:“我的老花鏡掉了一個腿,沒有它我什么也看不清楚。”我對母親說:“明天我給您買副新的。”母親笑了笑說:“好,好。”可是一個月、兩個月、一年多過去了,母親也沒戴上新的老花鏡……
1994年3月一天,冬季的涼意還沒有完全消失,村里人捎信來了,說母親病了,病得很重。我當時驚呆了,一句話也沒說,驅車就往家里趕。
到家后,母親已經昏迷不醒了。醫生診斷是“腦出血”,經過多方搶救也不見好轉,十五天后,母親就去世了。我手里拿著母親那副掉了腿的老花鏡,愧疚得如箭穿心一樣……對母親的遺憾是終生的遺憾。
咳,想起這些眼淚就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去年,熊岳望兒山建了一座“慈母館”,我花了近半年的工資將母親的畫像刻在慈母館顯著的位子上,并親筆書寫“香火暖母寒”五個大字。每年母親節,我便帶著女兒到慈母館給母親敬香,讓母親在九泉之下永遠享受人間的香火,因為母親的一生太冷了……
母親離開我也有兩年多了,那兩盆秋菊也不知去向了。昨天聽村里來的人說,哥哥在母親的墓前載了兩棵長青樹,又種了一些花草兒,我心里很高興。做后輩人了,在老人墓前放一些她生前喜歡的東西,不管是有用沒用,也算盡了一點孝心吧。
想到秋菊,更思念我的母親。她給我的太多了,而我還給她的太少太少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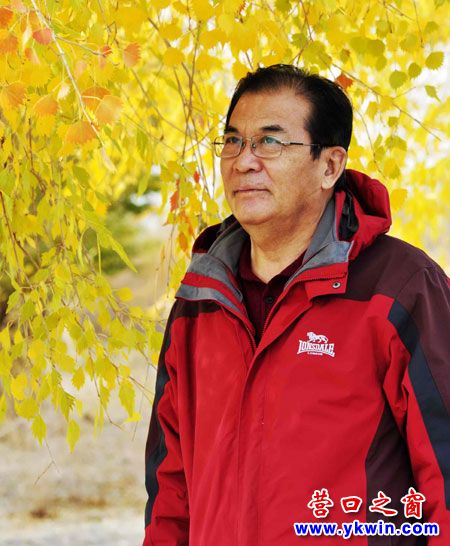
張冰先生簡歷:
張冰,遼寧營口市人,字耀松,筆名東南。作家、學者、詩人,一級散文家。研究生學歷,碩士學位。先后擔任中學語文教師,市政府部門副局長、局長,市人大專委會主任。兼任營口市作家協會副主席、南京中山文學院客座教授、營口市詩詞學會會長、中華詩詞學會理事、中國鄉土文學協會理事、王充閭文學研究中心理事長、關東十三友會會長等。現已出版詩集、散文集5部,主編學術研究專著1部,組織編寫文學研究專著3部。散文集《蘆葦》獲遼寧省二十世紀“豐收杯”三等獎、中國鄉土文學獎。其略傳收入《中國當代藝術名人大辭典》《中華人物大辭典》《中國人才世紀獻辭》《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名人錄》等10余部辭典。
供稿作者:張冰
原創發布:營口之窗官網
更多信息,請關注營口之窗公眾號:營網天下
版權聲明:營口之窗所有內容,轉載須注明來源,禁止截取改編使用。

上一篇:常憶舊時年——李同雁
下一篇:最后一頁